摘要:中篇小说《心的阴翳》是尾崎红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它以迥异于红叶之前的构文方式,描写了盲人按摩师佐之市对富家小姐久米的执念暗恋与苦恼,以及久米面对恋情的人生抉择与萌生的“心的阴翳”。本文在耙梳楫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小说所述“阴翳”的主体内涵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心的阴翳》文本进行重新考察,来探讨在江户传统文学和欧化风潮交错的时代背景下,尾崎红叶创作出此篇小说的真正用意所在。
关键词:尾崎红叶;心的阴翳;主体;内涵;
尾崎红叶(1867-1903)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著名小说家,他创作的中篇小说《心的阴翳》创竞于1893年上半年,分三十六次连续刊载于同年6月1日至7月11日(期间6月14日至6月19日一度停载)的主流报纸《读卖新闻》上,到了1894年5月由春阳堂出版发行单行本。《心的阴翳》是尾崎红叶中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小说主要讲述了盲人按摩师佐之市暗恋上了任职旅馆老板家的千金小姐久米,后来久米选择嫁给当地县议员的儿子喜一郎,陷入情感漩涡的佐之市却依然执念难忘,并由此催生了两人内心深处的“阴翳”。
根据已有资料显示,有关尾崎红叶小说《心的阴翳》的先行研究全都是在日本学界展开的[①],其所探讨到的主要问题归纳起来可分为:(1)人物佐之市的心理描写与红叶创作阶段的关系,(2)该小说对江户文学的继承与被影响,(3)该小说的近代性与自然主义文学的近代性的简要对比,(4)小说人物命运的设置与多重寓意的解读。其中关于《心的阴翳》的主体内涵寓意亦有所提及,具体到作品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或者默认)“心的阴翳”的主体所指的是小说男主人公佐之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专事尾崎红叶研究的冈保生和龟井秀雄。究其原因通常认为这是因为佐之市内心对久米偏执的暗恋遭遇失败,小说所描写的“阴翳”顺理成章地指男主人公佐之市内心的阴翳和失落。[②]毋庸置疑,以上论点的提出大多是研究者(读者)基于对兼具弱者和残障者双重身份的佐之市的深切同情,这其实可以划归到作品人物形象研究的范畴。另外,亦有少数学者认为“阴翳”的主体实质上指的是女主人公久米,主要理由有如“虽算不上是久米的爱情,但她的情却不是对丈夫喜一郎而是倾注给了佐之市。久米这样(噩梦困扰)是对佐之市是无意识的阴翳”[1],上论是在小说文本分析中对久米决定嫁人后所做噩梦与江户文学的关系进行考察时顺带提出来的,这无疑是对已有佐之市“阴翳”论调的反驳,但是因为原论目的是探讨小说与尾崎红叶创作阶段的关系,于是对该课题便没能继续进入更深层次的探析。
事实上,据笔者对《心的阴翳》文本进行统计,全文总共10回,第1至6回主要以佐之市为焦点,以全知叙事视角描述了佐之市坠入单恋之河到不能自拔的整个过程;到了第7至10回,则笔锋一转描述对象更换为佐之市的暗恋对象久米,同样以全知叙事描述了久米从决定嫁给实业青年家喜一郎到新婚夜不能释怀的苦恼。通过小说的全文布局来看,久米并非如冈保生所言是小说的配角,而是在小说后半部分转身成为小说的叙事主角,与佐之市一样,“心的阴翳”在最后也成为久米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扰。因此,本文在耙梳楫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小说所述“阴翳”的主体内涵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心的阴翳》文本进行重新考察,以探讨尾崎红叶创作出本篇小说的真正用意所在。
一
《心的阴翳》的原日文题目是“心の闇”。“心の闇”这个词在日语辞典《大辞泉》中主要有两个释义:其一是内心丧失平静、不能区分是非,其二是父母因过度挂念子女而引起的内心迷乱。结合尾崎红叶小说《心的阴翳》所述内容来看,其主要和第一条释义相关。关于第一点这在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就能找到相应依据:
①もすがら 月を見顔に もてなして 心の闇に 迷ふ頃かな(《山家集》卷中·恋640)
②搔き暗らす 心の闇に まどひにき 夢うつつとは世人さだめよ(《古今和歌集》恋3?644)
从上述例子可知,“心的阴翳”在古代文学中大多与爱情所带给恋人们内心的苦恼与困扰相关,而这种恋情又大多是以失恋而结束的,因而郁积成为心中不能超越的阴翳。无疑,上引①和②中“心の闇(心的阴翳)”一词的涵义所指为由于恋情而惑乱怅惘的心,这个意义层面上和“内心丧失平静、不能区分是非”有相同的所指。而该词在传统日本文学中多有借用,常被用来借喻相恋的双方在爱情中迷乱后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关于这一点,日本当代评论家坪内祐三也指出“心的阴翳”一词有着更为复杂的人文内涵,在论述过程中即举出尾崎红叶的恋爱小说《心的阴翳》,最后总结说“心的阴翳就是这样高深的语言”。[2]坪内佑三的原文本意是以“心的阴翳”一词为例,提示读者不要一看到词语就被其浅显的表层涵义所欺瞒,从而导致思维定势、对内涵的思索也止步于此,从而放弃了对事实深层真相的追求。而在此处提及尾崎红叶的同名小说,虽然不无偶然,但仍无疑是对《心的阴翳》这部小说恋爱主题的一种暗和。
二
回到尾崎红叶小说《心的阴翳》文本中来看,首先所指涉的主体就是小说主人公佐之市对久米多少带有偏执色彩的内心单恋,这是一种无法排遣的“心的阴翳”。由于佐之市的暗恋一直潜藏在心底,并未曾向心仪对象久米公开告白,所以该小说首先着力刻画的就是佐之市内心深处对久米的暗恋,这场爱恋从无到有、再从有到绝望,最后转化为佐之市内心的阴翳的整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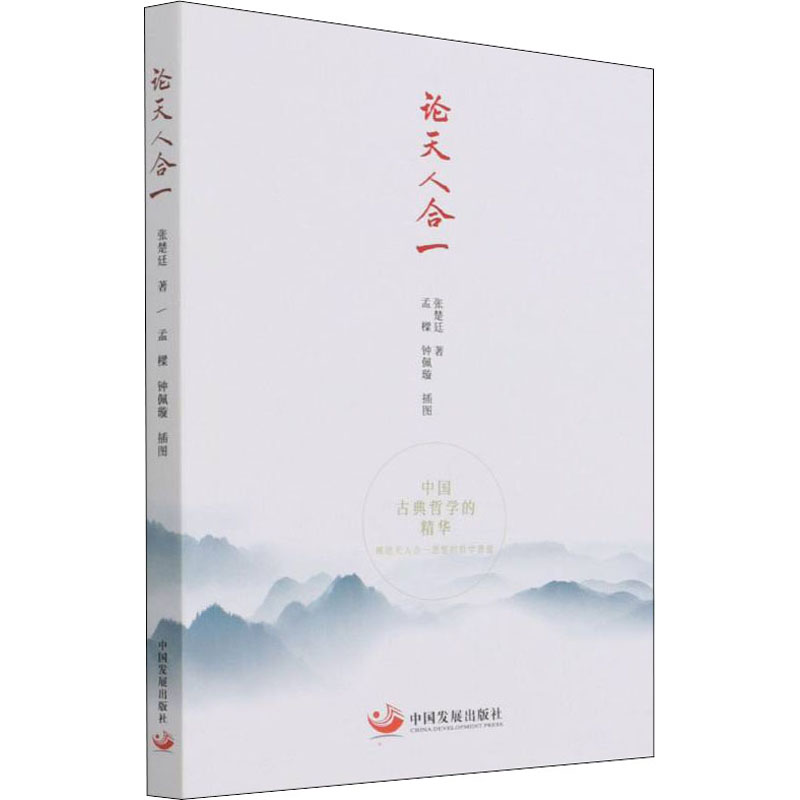
佐之市对久米产生爱慕,要从久米送给佐之市糕点这件事情说起。这日给客人按摩完毕的佐之市准备回家,老板家的独生女久米却突然召唤佐之市来自己的闺房喝茶,临末还送给他一包糕点。久米本身的无心之举却勾起了佐之市的无限好感。在小说中,这样描述佐之市在回家路上的情景:
门外月影稀疏,沉浸在无法看得见自身的半夜凄凉里,越是心寂越是任由心念驰骋。虽然这条路上通行数载,已经是毫无障碍,他仍一只手如获至宝地托着点心,一只手响亮地敲打着拐杖,沿着大路向西行走二町[③]路程,就距离佐之市家居住的地方不远了。
佐之市不假思索地唱道:
“即便是搭上性命也要在一起,
不在一起活着就没价值。”
他的声音并不高亢,却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他缩着脖子,往前走二三步,然后嘴里反复唱着同样的歌词。他唱完开始思量,思量好又开始唱,就这样到了家门前。[3]
上文中,佐之市的心情和所身处“半夜凄凉”的周围环境构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除了一系列的人物动作外,他唱出来“即便是搭上性命也要在一起,不在一起活着就没价值”的歌词也是人物心境的重要体现。如果说前半句是对这份恋情的向往,后半句则表述了佐之市对恋爱失败的假设。在这里,“活着就没价值”表现了佐之市对这份恋情一开始就隐含的担忧,也暗含了佐之市自感情一开始就埋下了“心的阴翳”的隐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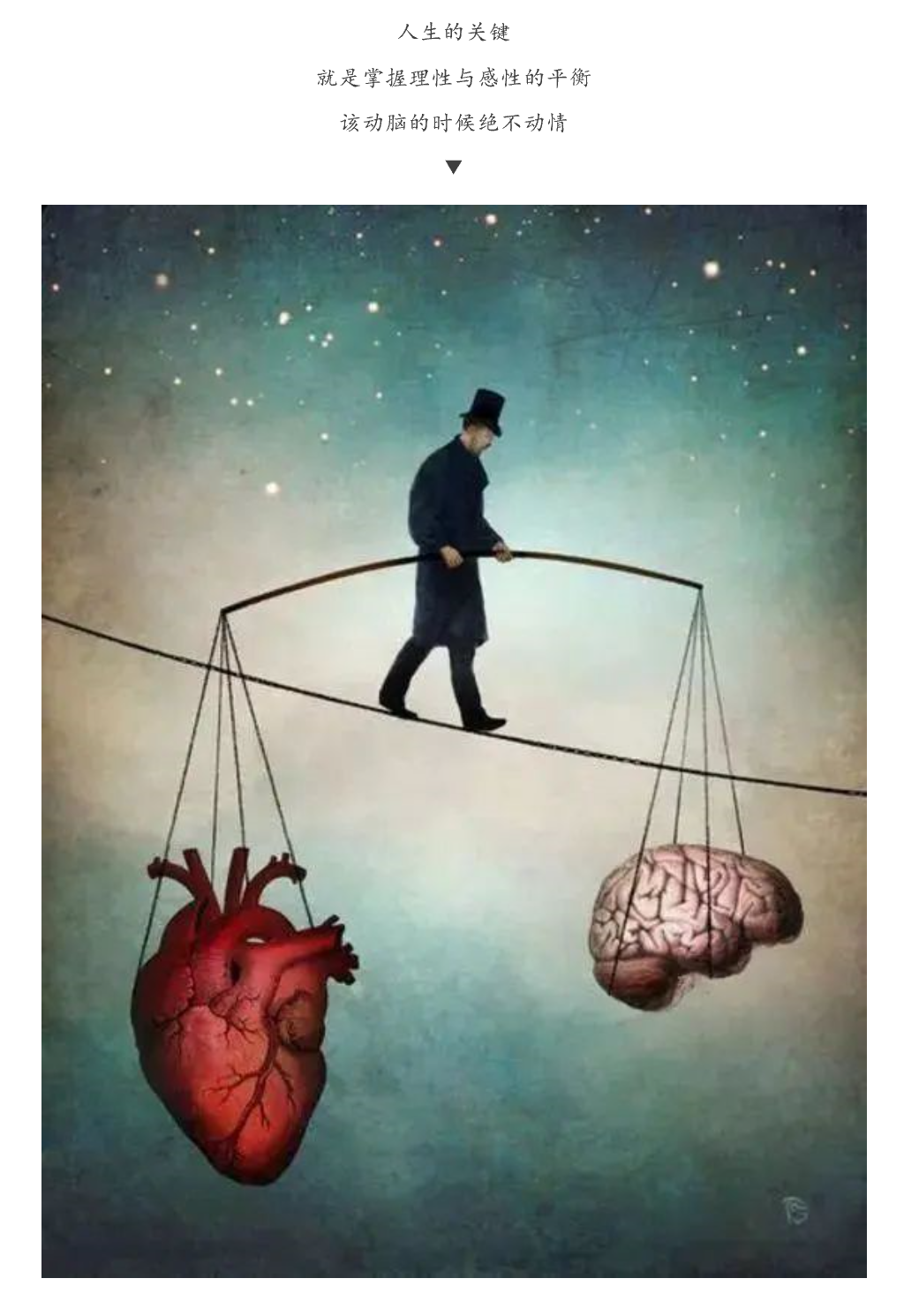
不言而喻,对于和久米之间的恋情,一直处于暗恋位置的佐之市始终是心存阴翳的。这点是和他自身的身体缺陷(后天生病导致的盲目)密切相关。佐之市自小不知道生父是谁,由艺妓出身的母亲阿民抚养长大。六岁的时候得了眼病,由于治疗不及时导致失明。后来在千束屋老板的帮助下,佐之市成为了盲人按摩师,从而过上了温饱生活。当他接受来自老板家千金小姐久米的那包糕点的时候,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与此同时,佐之市的内心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与久米在身份上的差异,久米的父亲给予过自己帮助,而且现在还是自己的老板,可谓是衣食父母。第二,自己一双盲目,虽然长相并不丑陋,但是“两眼凹陷处如同被胶粘住了似的”[4]。到了后来,佐之市到街上理发的时候,因听到对久米的调笑在与社会闲散吉五郎发生冲突被打的时候,他首先“想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千束屋便一点也不后悔,这是武士对主家的忠义”[5]。可见佐之市对于自己的恋情仍然是有所顾虑的。在听到诋毁久米的流言的时候他能挺身而出,来捍卫久米小姐的品格声誉;在被吉五郎殴打后,却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武士对主家的忠义”,这种行为与思想上的矛盾一直伴随着这场恋爱发生的全过程,也成为人物导致佐之市“心的阴翳”的首要原因。
另外,佐之市的一双盲目则是其恋情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在小说中的体现十分明显。如小说开篇描述男女主人公的相遇:
他……一边听着院子里喷水的声音,一边往右一拐,面前就是老板的卧室。在入口处他猫下腰,没有人和他说话。即便是搭腔也没有人应对,耳朵里只有钟表撞击发出的声响。佐之市苦笑一下,屋子里没人。就在他慢慢地回转要走的时刻,突然听到了身后不知是谁的脚步声。他不禁停下脚步,就听到了听上去总感到娇滴滴的声音:“佐之市”![6]
在此,作者采用了全景式限知的叙事模式描述了人物佐之市对外在事物的感知过程。由于佐之市视觉的缺失,于是文本的展开则是在对佐之市听觉的把握上描述的。对于不擅言辞表达和失去视觉观感的佐之市,听觉就成了唯一与外界感知、认知自我的途径。但是,听觉只是对佐之市个人而言的,对于其他人物而言,他们根本无法体味佐之市内心的真实感受,自然也就无从理解佐之市的内心世界。不被周围环境所理解,就成为佐之市“心的阴翳”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佐之市的最后一次出场,如下:
佐之市此时正好唱道:
“即便是搭上性命也要在一起,
不在一起活着就没价值。”
虽然没有人听见,只是他自己的独唱。他未必会选择死,只要性命存在就要追逐金钱,他每天都去千束屋按摩。母亲阿民也不逊色儿子,她用自己的小积蓄做起了高利贷生意,母子的买卖都很繁昌。[7]
这一幕发生在久米的新婚之夜,得知对爱恋无望之后,佐之市孤自从久米的婚房周围走过,他又唱起了与接受久米糕点后那晚回家途中的唱词:“即便是搭上性命也要在一起,不在一起活着就没价值”。但是与当时满怀信心的情形恰恰相反,这次佐之市不得不面对的是这场暗恋的幻灭。如果上次是要表达必须和久米相爱、在一起生活的话,这次则是承认了暗恋的最终失败,自己从此将面对的是“不在一起活着”的“没有价值”的生存状态。在小说结局里,佐之市仍然继续着在千束屋按摩的工作,母亲阿民也做起了高利贷生意,追逐买卖上的成功。虽然没有描述佐之市的内心感受,但是恋情幻灭的事实,无疑是此后佐之市永远挥之不去的“心的阴翳”。
三
在小说《心的阴翳》中,主要在前6回以佐之市为聚焦对象,到了第7回则笔锋一转,开始从久米待嫁闺中说起,直至全文结束。对于这样的文本构架布置,冈保生已经注意到,在尾崎红叶的传记中他是这样概述这篇小说的所写内容的:
《心的阴翳》讲述了年轻的盲人按摩师爱慕上供职旅馆老板家的女儿的故事。老板家女儿结婚后,按摩师仍然持续爱恋,年轻的妻子在梦中反复梦到按摩师,从而坠入疑神疑鬼的状态。[8]
从划线部分来看,冈保生对《心的阴翳》的小说结构有所察觉,但是遗憾的是,接下来他引入了本间久雄在《续明治文学史》中所论述的该小说中的心理描写特征,继而转为探讨佐之市单方面的恋爱心境的细微描写,而没有对久米这个人物的出场设置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近年来,亦有学者开始关注《心的阴翳》中久米形象的相关研究,例如通过对久米相亲择偶标准(例如有知事下属官吏、巡查、失业青年家等)来考察小说文本中男子形象设置中的近代与反近代问题[9],认为久米是在尝试构建近代意义上的“家”(嫁给青年实业家喜一郎),而不是选择自由恋爱(佐之市)[10],以及对久米梦魇的考察,从而探寻其与江户文学的关系[11]。
对于久米对佐之市是否有恋情存在,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小说文本中也没用明确说到,但是通过一些细节仍可一窥端倪。小说中两人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久米用“听上去总感到娇滴滴的声音”(参见引文[8])呼唤佐之市;第二次见面时,要去相亲久米正在换衣服,使得目不能视的佐之市还能分辨出“感觉得到她正在更换和服,不知道是系和服下摆还是裙裤的带子的声音,听上去十分响亮,不知道和服还是什么的衣物上的阵阵芬香扑鼻而来”[12]。对于以上的行为,无疑是久米有意为之,但是其究竟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尊贵、对佐之市的挑逗,还是潜意识对佐之市的萌生好感,至此还是很难一下子作出定论。文本中紧接着(第4回),佐之市躲藏在阁楼阴影处偷听久米的相亲谈话,后被人发现继而遭到知事随从推搡之时,久米“对于佐之市那可怜的样子再也看不下去了,久米对知事大声喊道:‘饶了他吧’!就在这些醉酒汉们被惊吓住了的时候,久米拾起佐之市的手,拉着他从人群包围中冲了出来,从楼梯上拽到房间里面。”[13]从这个例子来看,情急之下久米选择以“美救英雄”的反常态模式是基于什么样的初衷,除了佐之市是千束屋客栈里的小伙计外,其内心深处潜意识中的“恋情”估计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吧!
同样还有其他的例证,就是久米最后同时梦到喜一郎和佐之市的描述(第8回)。在有关的先行考察中,村松定孝认为佐之市在久米梦魇中的登场,这是“久米潜意识有欲求要确认来自佐之市的恋情”。[14]这种推断是极其中肯的。因为当时久米已经决定嫁人,未婚夫是当地县议员的儿子同时也是具有“近代”意义身份的青年实业家的喜一郎。但是在久米梦中,先是梦到了佐之市,然后出现了喜一郎,最后又突然变化为佐之市,于是久米惊梦。梦中人物的反复变换自然是久米在内心的不断提示和潜意识中对自己恋情的抉择过程,从梦境人物转换来看,与喜一郎相较,久米还是对佐之市更有感觉,佐之市在梦中的两次出现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现实中,久米和喜一郎已经有了婚约,出嫁在即,内心“确认”出来的结果却是佐之市,与现实的巨大差异无疑使得久米惊梦心悸。无奈也罢,无力也罢,她还是遵从父母的安排,选择了与喜一郎进入婚姻,这样的同时意味着久米选择了“心的阴翳”。
新婚夜里,久米不能入睡,当得知是佐之市徘徊在自己的寓所外面的时候,久米“心的阴翳”自然加重。小说结局中提到,婚后久米和佐之市二人再也没有见面。然而久米每月都有两三次会梦到佐之市。“有时候如死了的人一样奄奄一息,有的时候如同妖怪表情恐怖,因为有怨气所以才托梦的。哭着醒来的时候也有。每次梦到的长相都不曾变化,心情却都是一个,不能割舍那没有实现的恋情。”[15]这说明对久米而言,与佐之市的关系是“那没有实现的恋情”,对佐之市的“不能割舍”正是导致久米“心的阴翳”的最根本原因。
四
在《心的阴翳》的末尾,如是写道:
久米与其说是做了奇怪的梦,不如说是对佐之市的猜疑,她也没有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佐之市的最新消息。仅仅是怀疑,真伪难辨。
不说出来却会陷入思恋,猜疑又令人畏惧。这就是恋爱,心的阴翳。[16]
对于自己对佐之市的感觉,久米始终是迷乱的。由于佐之市并没有以任何的方式表达对自己恋情,因此久米只能局限于“仅仅是怀疑”。小说结尾最后一段,“不说出来却会陷入思恋”,如前述学者一般认为写的是佐之市带偏执色彩的片面暗恋,而根据以上分析来看,“猜疑又令人畏惧”无疑指的是小说后半部分篇幅重点描述的久米的“心的阴翳”了。正如小说最后一句所隐含那样,这样一场使得双方都遭受内心煎熬、却不能穷其究竟的恋爱,带给佐之市和久米的无疑都是“心的阴翳”。
对于尾崎红叶之所以会创作这样一个题材的恋爱小说的原因,有必要对尾崎红叶这一时期创作情况进行梳理。《心的阴翳》发表于1893年6月至7月期间,一边写作一边发表,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在《读卖新闻》刊登。根据此时期尾崎红叶文学发表可知,1892年至1893年6月间发表的翻案作品[④]主要有3篇,分别是戏剧《夏小袖》(1892.5)、《恋之病》(1892.11-1893.10)和童话《三根头发》(1893.1)。对此当时文坛也不断有声音质疑,认为“红叶才思枯竭,没有写作素材,其证据就是这一时期所写作品皆是从外国通俗小说翻案而来的”。[17]尾崎红叶翻案的前两个作品底本分别是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的《悭吝人》和《被打出来的医生》[⑤],《三根头发》则翻案于德国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的《有三根金头发的鬼》。这三篇翻案作品中,只有《恋之病》写的是纯粹的爱情题材,其故事梗概是富家小姐阿类为了与心仪的男子弥三郎结婚,就假装自己不能发声,在假扮成医生的七兵卫的巧妙配合下后来与弥三郎约会并最终成功私奔。通过对比这篇小说和《心的阴翳》的情节,虽然二者同属于恋爱题材,但是两个作品的故事构架却朝着相反的两极发展:阿类大胆果敢,敢爱敢恨,久米疑虑多思,遵从父母媒妁的安排,不愿意追求自由的恋爱;阿类收获了爱情,久米陷入了阴翳。阿类患了幸福的“恋之病”,久米却坠入不幸的“心的阴翳”终不能自拔。从这个意味来看,《心的阴翳》的创作极有可能参照了翻案作品《恋之病》的故事架构,而故事情节朝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则只是尾崎红叶不同的写作策略与布局手段体现。
另外,应该提及的是此时日本文学的发展状况。尽管明治维新已经开始二十余年,但是继承江户戏作文学[⑥]审美情趣发展而来的明治戏作文学仍占据文坛中心位置。[18]这一现象具体到尾崎红叶身上就是创作了一系列戏作痕迹浓重的小说。就在《心的阴翳》发表前的1892年,尾崎红叶连续发表了《二人女房》和《三人妻》等被认为是江户戏作文学色彩极为浓厚的小说,从而招致以《国民之友》杂志的八面楼主人[⑦]为代表的文坛的连番诘难。但是在同时期活跃于文坛的其他作家的境遇则有所不同,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1885)至此已发表八年,当时文坛齐名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1889)、森鸥外的《舞姬》(1890)、幸田露伴的《五重塔》(1891)都纷纷发表,无论从题材还是从文体方面都尝试着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完成自我的近代蜕变。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尾崎红叶的《伽罗枕》(1890)和《三人妻》(1892)却仍陶醉于江户文学传统的审美情趣中,此举遭到同人激烈批判是可想而知的。早在之前的1889年12月,尾崎红叶在高田早苗的介绍下,加盟《读卖新闻》社,成为报纸小说家。[19]此时对于来自其他刊物不间断的文学批评甚至矛头对准尾崎红叶的人身攻击,活跃于报刊业的他不可能毫不在意。但是如何面对和处理,的确是需要好好思考一番的。所以此时期他花费大量精力,全副身心投身于外国小说的翻案也绝非事出偶然。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文学中的翻案现象并非是简单的对应翻译,更多的是将中国或者西欧文学作品的内容和情节改编、嫁接到此时的日本文学中,这属于一种“功利的文学样式,……(但却)意味着发现新小说的方法”。[20]其中的风俗、地点、人名都相应发生改变,《恋之病》就是如此,将法国背景的爱情喜剧改头换面移植到日本的明治时代。如前述,《恋之病》和《心的阴翳》同属于恋爱题材,后者通过对前者进行相反方向式的“二次翻案”,受到启发,将之呈现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日本恋爱悲剧就变得成为可能。
之外,也有学者指出《心的阴翳》中红叶对官员的批判,因为官僚阶层在久米生活中的不断出现成为导致佐之市的恋爱最终失败的原因[21],而官僚正是作为日本明治维新的近代产物经常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中。据此可以推断出尾崎红叶对于西方文明还是持抵牾态度的。面对当时的文坛态势,在发表《心的阴翳》前后,处于创作瓶颈中的尾崎红叶是苦恼的,如何对江户传统文学和袭面而来欧化思潮进行整合,并运用到这一时期的具体文学创作中,对于当时的尾崎红叶而言无疑是极为艰难的,此时他唯有通过不断的文学实践来体悟。1893年6月至7月,《心的阴翳》在《读卖新闻》连载发表,日本文坛几乎是同一时间一改往日论调,突然间赞扬声不绝于耳,认为此篇是“红叶文学的杰作”[22],其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在写实主义文风在文坛大行其道的当时更是备受推崇,但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作家尾崎红叶的“心的阴翳”有几人能够真正体悟得到就不得而知了。
[①]据笔者搜集材料统计,以该小说为题的论文主要有8篇,全部为日语论文,在小说内文引入本论时全部由笔者译出:(1)土佐亨.心の闇——その近代小説性[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74(3): 127-131;(2)木村有美子.尾崎紅葉『心の闇』一[J].樟蔭国文学,1994(3):31-43;(3)木谷喜美枝.尾崎紅葉「心の闇」小論[J].和洋國文研究,1997(3):38-46;(4)坂井美紀.尾崎紅葉『心の闇』についての考察[J].Comparatio,2001(5):
11-17;(5)木村有美子.尾崎紅葉『心の闇』二[J].羽衣國,2003(3):48-62;(6)馬場美佳.清玄の行方--尾崎紅葉「心の闇」論 (特集:さまざまな「小説」観)[J].稿本近代文学,2003(12):1-16;(7)木村有美子.尾崎紅葉『心の闇』三[J].樟蔭国文学,2004(3):23-38;(8)野中双葉.尾崎紅葉「心の闇」論:新たな恋物語としての可能性[C].東アジア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化研究15,2012:187-203.
[②]参见①岡保生.明治文壇の雄:尾崎紅葉[M].東京:新典社,1984:202.②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亀井秀雄解説[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501.
[③]日本旧有长度单位。按照计量规定,1町约为60步(6尺为1步)。1891年规定1.2km为11町,1町约合109.09m。
[④]日本的翻案文学发端于江户时期对中国文言·白话小说的引进介绍,与现代认为的翻译不同的是翻案保存了原作的内容和情节模式,而对其中具体的风俗、地名、人名等则移植为本国相应的风俗、地名和人名,例如三游亭圆朝的《牡丹灯笼》即就是对明小说《剪灯新话》的翻案。到了明治时代,翻案的对象则转为欧美作品,代表作家就有本论文所考察的明治作家尾崎红叶。
[⑤]此处题名翻译参照赵少侯中文译本,二文同收录于《莫里哀喜剧选》(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据笔者调查,此译作采用直译译出,与法语版本全文基本保持一致。
[⑥]戏作文学又称戏作,是日本近世后期对兴盛于18世纪后半期到江户末期的出版物的总称。此种文学模式至明治初期仍一度繁盛,包含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读本、草双纸等文学样式,由于风格以模仿和嘲讽见多,其作者多被称为“戏作者”,代表人物有式亭三马、十舍返一九和假名垣鲁文等。戏作文学流传到明治中期逐渐式微。
[⑦]即日本小说评论家宫崎湖处子(1864-1922),是倡导日本近代诗创作的先驱,小说家,他对尾崎红叶的批评主要针对对其“近代性”欠缺和对元禄文学的痴迷而展开。
[ 参考文献]
[1] 坂井美紀.尾崎紅葉『心の闇』についての考察[J].Comparatio,2001(5):15.
[2] 坪内祐三.『心の闇』の本当の意味を教えてあげよう[J].文藝春秋,2006(3):351.
[3]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254.
[4]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248.
[5]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278.
[6]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248-249.
[7]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300-301.
[8] 岡保生.明治文壇の雄:尾崎紅葉[M].東京:新典社,1984:202.
[9] 木村有美子.尾崎紅葉「心の闇」私論(一)[J].樟蔭国文学31,1994:36-37.
[10] 菅聡子.「心の闇」試論――その近代小説性[J].国文学,1974(3):131.
[11] 坂井美紀.尾崎紅葉『心の闇』についての考察[J].Comparatio,2001(5):15.
[12]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264.
[13]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269.
[14] 村松定孝.紅葉の中の“愛”[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78(5):60.
[15]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300.
[16] 尾崎紅葉.紅葉全集?巻四[M].大岡信,岡保生など編.東京:岩波書店,1994:301.
[17] 田山花袋.近代の小説[M].東京:大東出版社,1941:78.
[18] 越智治雄.文学の近代[M].東京:砂子屋書房,1986:62.
[19] 尾崎紅葉,泉鏡花.日本の文学4[M].東京:中央公論社,1969:511.
[20] 三好行雄.日本文学の近代と反近代[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6:129.
[21] 大屋幸世.紅葉のリアリズム[M].三好行雄,竹盛天雄編.東京:有斐閣双書,1977:49.
[22] 土佐亨.心の闇——その近代小説性[J].国文学: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974(3):127;
注:上文发表于《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1期,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