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 30年前的那场爆炸,至今还能令我们为之震颤。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于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在实验中发生爆炸,致使大量高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造成几十万人紧急撤离。而爆炸当天就有5位摄影师进入了切尔诺贝利现场,用照片向世界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景象,在之后的30年里,又有无数摄影师不顾辐射的危险回到切尔诺贝利,记录这场史上最严重核事故对当地居民和生态的影响。腾讯特邀曾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的三位摄影师Gerd Ludwig,Donald Weber和Arthur Bondar,向我们讲述那张最令他们印象最深刻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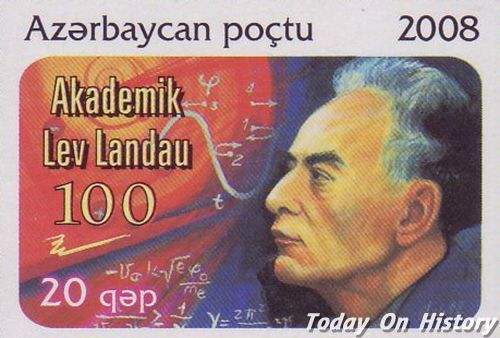
核辐射反应堆里的15分钟,那一刻,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工人等待进入一个叫做“除氧器栈”的区域,计划在里面的混凝土上钻孔以安装支撑梁,用来稳定已经向外倾斜、有可能坍塌的西墙,2005年。(图片:Gerd Ludwig/美国国家地理)九十年代初,罕有步入切尔诺贝利的机会。乌克兰政府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走到哪儿,军方就跟到哪儿。尽管他们遵循着各种指令,却也在尽量理解我想要从当局得到拍摄许可的努力,而当局显然是要尽可能的切断一切可能性。当时,我尚未被允许接近反应堆,更不必谈进入切尔诺贝利。
转折发生在2005年。我穿戴上了保护装备,包括非常先进的盖格计数器和辐射测量仪,又套了一层3-4毫米厚的塑料工作服,跟着六个工作人员进入了反应堆。他们要在混凝土上钻孔,以加固反应堆的屋顶和西墙,因此还额外穿戴了防毒面具和氧气罩。我们的动作得非常迅速。那个地方的辐射实在太高,尽管我们有防护设备,一天也只能进去15分钟。
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严峻的拍摄任务了。空间很暗,嘈杂,能让人患上幽闭恐惧症。当我们快速地走过散落着电线、金属丝和其他碎屑的昏暗隧道时,我几次差点被绊倒。一边拍照,我还要一边避开电钻产生的火花,因为里面都带着高度污染的混凝土灰尘。我知道我只有不到15分钟的时间来拍摄出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向世人展示此种场景,而且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了。想到这些,我的肾上腺素飙升。
然而,原本计划的15分钟刚刚过半,我们的盖革计数器和辐射剂量计就响了起来,气氛顿时更紧张了。测量计的哔哔声就像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演唱会,提醒着我们:时间到了。我在求生本能和摄影师总想多停留一会的渴望间挣扎着,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最后能集中注意力,高效、快速而不草率的工作是我必须面对的挑战。
展开全文
2013年时,我再次进入了反应堆,比2005年走的还要深。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我们停在了一扇很重的金属门前,工程师示意我只有很短的时间拍照。然而,他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打开那扇卡住的门。我开始觉得紧张。房间里面是全黑的,仅有的光源来自我们头顶的探照灯。乱七八糟的电线挡住了我的视线,我隐约辨认出房间最远处墙上有一个时钟。我只拍摄了几帧照片,还在等我的闪光灯充电时,工程师就把我拉了出来。我赶紧查看我的照片,失焦!我恳求他让我再进去一次,最后,他给了我几秒钟的时间去拍摄那个钟表,钟表上的时间显示为凌晨1时23分58秒,正是1986年4月26日在这栋楼里发生爆炸的时间。那一刻,时间永远的停止了。
Gerd Ludwig,国家地理摄影师,在20年间九次拍摄切尔诺贝利地区,出版摄影书《切尔诺贝利深长的影子》。
如果我在这里居住,会这般生活么?
砍完柴,维克多和朋友在河边休息,2005年4月25日。(图片:Donald Weber)
1986年,12岁的我因患了严重肺炎卧床不起,只靠趴着听收音机打发时间。那时候我深信,不管是在加拿大、美国还是欧洲,我们都会死于某种可怖的核灾难,这个灾难极有可能是核战争;特别是身处加拿大的我们一定会卒于美苏两国的交火。电视持续向我们传递世界岌岌可危,核战争的阴影时刻笼罩的讯息。许多应急广播系统在不断被测试,像电影《洗劫后》和《赤色黎明》里那样;《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等杂志的封面也一直宣称核破坏、核战争即将到来,死亡就在我们面前。
杞人忧天的我,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这一切都无助于抚慰我的恐惧。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86年4月26日的几天后,电波里传来切尔诺贝利大灾难的消息,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将死在一场苏联造成核灾难里!
在电影术语中,这叫“起源故事”, 用来交代一个角色的背景,和他或她如何变成如今的样子。我的起源故事也从那一刻展开了。我对所有俄罗斯、苏联、共产党的东西简直着了迷,如饥似渴地沉浸在相关的杂志、书刊和电影里。我想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亲自去看到这一切。而且,就像我在杂志中看到的那样,我会用相机记录下所见所闻。
最终,我终于到达了切尔诺贝利,见到了最具毁灭性核灾难的现场,也是我对一切核恐惧的隐秘之源。2005年,我在切尔诺贝利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短途旅行。我对历史、理论和原因都毫无兴趣,去只是想看看那里有什么。我的问题很简单:
1核事故发生后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2006年的冬天,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和当地人共同生活、工作。开着一辆破旧的拉达汽车,努力让自己适应节奏缓慢的乡村生活,吃喝如同当地人;主要以土豆和伏特加过活。
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认识了维克多,他跟我同岁,甚至生日只相差了几天。之后我多次访问切尔诺贝利的时候都会和维克多见面。我可能总共给他拍了十次照,这张照片是一开始的时候拍的。他邀请我到河边,他和朋友们砍柴后在那里小憩。砍柴是那个地方仅有的,并且收入很微薄的的工作。切尔诺贝利一片寂静,甚至没有鸟鸣,却处处洋溢着劫后余生的喜悦。因此那天,我们喝了酒,一杯接着一杯地开怀畅饮。
和维克多在一起时,我禁不住总是细细观察着他:是否他即是我?如果我在这里居住,会这般生活么?对此,我无法回答,但这却是我喜欢这张照片地原因。对我来说,这是一副自画像,一个在做着狂热的梦的我。
Donald Weber,加拿大纪实摄影师,多次前往切尔诺贝利记录核事故后人们的日常生活,著有《混蛋伊甸园,我们的切尔诺贝利》。
这艘在白杨树和雾气间漂浮着的破旧的船,是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象征。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Teremzy村里一艘被遗弃的船,2010年。(图片:Arthur Bondar/VII图片社“导师计划”项目学员)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爆炸的时候,我才三岁。对辐射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第一次去切尔诺贝利是在2007年,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做摄影记者,去报道一个政客在当地的活动,自那以后,我就不断找机会返回切尔诺贝利。
这张照片来自《茵陈的影子》,是我过去八年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附近的村庄拍摄的一个集合。那一次,我在隔离区的一个村子里住了整整一周,一天都没有离开过。
返回切尔诺贝利定居的这些人都很友善, 大自然随处可见,还能享受绝对的安静。在那里,我的生活非常舒适和安逸。一天清晨,我散步去了普里皮亚季河,雾气笼罩着整个河岸,我远远看到一个船型的东西,走了过去开始拍摄。那艘船很大,布满了灰尘,拍摄完毕后,我一转身,又在不远几米处的白杨树林中看到了一艘小船。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村里其实有一个小港口,在灾难发生前,好多船都停泊在这里。爆炸发生后人们被紧急撤离,而这艘正在接受检修的船被留了下来。
正是在这艘船附近,我感受到了隔离区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但我拍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没有一张能表达我当时强烈的情绪。最终,我将镜头稍微上倾,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度,从下往上拍到了这张照片。那个无法言喻的感觉也终于明了了:这艘在白杨树和雾气间漂浮着的破旧的船,对我来说,就是曾经庞大的苏联的象征,也是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时代的象征。
Arthur Bondar,乌克兰摄影师,长期拍摄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附近村落的自然和居民生活,出版摄影书《茵陈的阴影》。
距切尔诺贝利隔离区1.5公里的一个叫做Straholesie的村子里,渔民们刚从结了冰的河里打完鱼,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切尔诺贝利四号反应堆附近的水库里,鱼因为受到高度辐射而体型巨大。
隔离区内一户人家家中摆放的肖像和家庭合影。
在隔离区附近的Straholisya村,人们正在举行葬礼。
切尔诺贝利市地上发现的一张工作证。
一座被野葡萄藤覆盖的房子。
一张1986年的隔离区地图。隔离区是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圆心向外30公里内的区域,整片土地被铁丝网包围。 谷雨:为什么给这个项目起名《茵陈的阴影》?
Arthur Bondar: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很多人相信,对这场悲剧的第一个警示出现在《圣经》中:“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来自《启示录》八章 10-11节。切尔诺贝利(Chernobyl)市的名字就来源于这种叫做茵陈的植物。
谷雨:切尔诺贝利地区的生态好像是你项目的侧重点,为什么?
Arthur Bondar:是的,这个项目主要侧重记录了隔离区与附近村落的自然及居住者的状况。 当你来到一个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的地方,感觉是很奇怪的。2007年时我基本听不到小鸟或其他动物的叫声,现在,这些声音逐渐多了起来。大自然的自我愈合能力是很神奇的。
在隔离区的土地上,你能感受到自然是多么的强大,而人类又有多么的脆弱。切尔诺贝利是一个很可怕的例子,让我们见识到人们可以多么轻而易举的毁掉一切,失去生活的平衡。
谷雨:我看了这个项目的多媒体视频,也许是配乐的原因,照片里的切尔诺贝利给我的感觉很神秘,甚至有一点恐怖。这是你想到读者感受到的吗?
Arthur Bondar:是的。整个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充满了神秘感,我们对它的了解太少了,只知道:隔离区充满辐射,而辐射是危险的。很多科学家仍在研究隔离区内辐射的威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去拍摄会发现什么。我觉得可以把辐射和信仰这两个概念做比较,它们既看不到也摸不到,但你明白它们一直在你身边。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就是一个辐射与信仰并行的地方,这营造出一种很强烈的神秘感。
谷雨:从你的照片看来,在切尔诺贝利定居的人都是老人。为什么他们会重新回到哪里,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年轻人在哪儿?
Arthur Bondar:悲剧发生的几天后,苏联政府决定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30千米内的人撤离,这里面包括许多村庄。当然,没有人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部队来人把人们扔出了他们的家,但是人们还是非法的回来了。后来苏联政府决定给老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去,并给了他们“自主定居者”的身份。直到今天,年轻人仍然不可以在隔离区居住。
谷雨:当地人和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Arthur Bondar:大多数的自主定居者都信奉宗教,对上帝的信仰帮助很多人度过了难关,而且大多数定居者认为,那些搬离隔离区的家的人,最后都因为过于恐惧辐射和思念家乡郁郁而死,而不是因为受辐射过度死掉的。在有教堂的地方人们更是绝对的相信上帝,认为是上帝拯救了他们。
Nykolay Yakushyn是Yllynskaya教堂的一名神父,这个教堂是切尔诺贝利唯一还开着的教堂了。他说:“如果你不尊重隔离区,它肯定会杀了你,但如果你对在这里遭受过苦难和死去的人充满了爱和怜悯之心,隔离区是不会碰你的。”
2谁清理了核辐射?
2016年4月26日,是切尔诺贝利灾难30周年纪念日。任何灾难,第一时间感到现场的人,往往是最悲情的角色。站在切尔诺贝利爆炸的4号核反应堆的楼顶,你只要呆上40秒,所接受的辐射量就是一生所能接受辐射量的最大值。而第一时间前往楼顶作业的清理者就有28人在1986年当年死亡,随后60万人加入清理行动……
封面图:切尔诺贝利清理工人清理3号反应堆的顶部。Igor Kostin/Corbis/视觉中国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代表作之一《切尔诺贝利的悲鸣》,第一章节就是一名切尔诺贝利消防员妻子的讲述,有人对她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等于坐在核子反应炉旁边”。她的丈夫在爆炸发生后第一时间前往核反应堆处置,她最终眼看着丈夫在超量辐射的作用下,在几周内慢慢死去。他接受了1600伦琴的辐射,而400伦琴就能置人于死地。图为进入核爆炸现场10天之后,一名消防员的身体。(由美国骨髓移植专家Robert P. Gale拍摄)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6分,曾被认为最可靠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核电事故。其影响之深远,远非今天的人们可以准确预测,但事故发生之后的短时间内,那些第一时间冲到现场的消防员、士兵、志愿者,却足以被称为“拯救世界的人”。图为摄影师Igor Kostin在爆炸第一线拍摄的被炸毁的4号反应堆。因为来自脚下辐射太强,导致照片下方出现了白光条纹。(Igor Kostin/Corbis/视觉中国)
4号反应堆爆炸之后,屋顶上到处散落着石墨块,石墨是作为原子反应堆的减速剂使用的。一开始,机器人被派到屋顶清理碎片,但几天之后,德国产的、日本产的、苏联为探索火星设计的机器人在高辐射下都无法工作。(Igor Kostin/Corbis/视觉中国)
于是,这个工作落到了人的手里。房顶的放射达到200西弗/小时,他们必须在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跑上楼顶,清理几铲子碎块,然后另外的人继续跑上来接替他们。他们因此被成为“生化机器人”。虽然辐射无法用肉眼看见和感知,但他们几乎立刻感到眼睛的刺痛、满嘴的铅味。GETTY
在楼顶,你只要呆上40秒,所接受到的辐射量就是一生所能接受辐射量的最大值。苏联政府并没有为他们提供防护服,那些进入高辐射区的人员只能自己想办法。一些工人只能用几毫米厚的铅板做成围裙套在棉质工作服外,这样一来至少可以保护脊柱和骨髓。许多清理者后来死了,其中有28人在1986年当年就死去。(Igor Kostin/Corbis/视觉中国)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政府数年间派出60万名工人前往灾区,负责消除核事故产生的可怕后果,他们的职责包括:清理高强度辐射的碎块、阻止核反应继续进行、防止核物质扩散、测量核电站周边辐射水平、搭建封阻4号反应堆的“石棺”,他们被统称为“Liquidators(清理者)”,他们中有士兵、消防员、飞行员、专家、工程师、核电站工作人员……图为一名“清理者”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的婴儿是在清理工作中发现的。(Igor Kostin/Corbis/视觉中国)
为防止核辐射粉尘更大范围地扩散,飞行员在反应堆上空进行抛洒抑尘剂作业。
飞行员的座椅上垫了铅板,以阻挡来自地下的辐射。
参与清理工作的坦克都包上了层层铅板。
从4月27日开始,当局组织军用直升机投下近2000吨碳化硼和沙子,反应堆内的链式反应终于停止。而最终直升机的总运量达5000吨。1个月后,放射性排放量才得以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最后,米格直升机将重达35吨的盖子吊放到反应堆顶部,构成一个将辐射阻隔的“石棺”。图为直升机吊着材料飞往4号反应堆。(Corbis/视觉中国)
很多人抱着“我要报效祖国”“我是军人”“我是共产党员”的信念去到那里。有的士兵因为年轻,还未生小孩而拒绝去,遭到羞辱和惩罚。尽管他们获得的酬劳是平常的数倍,但当有的士兵提着满箱子的钱回去,却发现妻子和孩子走了。图为反应堆爆炸后,一组“清理者”站成一排,准备前往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电站屋顶执行清理工作。(Igor Kostin/Corbis/视觉中国)
死亡的人大部份是消防队员和救护员,他们一开始并没有被告知核辐射的危险程度到底有多大,在作业中,他们无法知道自己吸收了多少辐射,只被告知:你不能再继续了。即使被送进医院,他们也被隐瞒了所遭受的辐射剂量。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警告不要将切尔诺贝利的情况向外界透露。图为一群“清理者”的合影。
“在那种时候,俄罗斯展现了它有多伟大,有多独特,我们永远不是荷兰或德国,不会有平整的柏油路或整齐的草坪,但是我们永远不缺牺牲奉献的英雄。”图为一群建造石棺的“清理者”在4号反应堆前合影,横幅上写着: 我们一定履行政府的命令!AP
据联合国“切尔诺贝利论坛”提供的一份报告显示,其中明确因遭受辐射而去世的清理者大约有4000名。图为一群“清理者”的合影,其中有人还带着自己的木吉他。
清理工作结束后,1350多辆苏联的军用直升机、巴士、推土机、油罐车、运输车、消防车和救护车,因沾染了大量放射物,而不得不弃用,只能安置在隔离区内。它们都不是机械,而是一个个核辐射“发射器”。AP
因沾染了大量放射物而弃用的消防车辆。REUTERS
那些死去的“清理者”躺进了特制的铅制的棺材里,他们的坟墓里灌进了混凝土,好将他们有着强烈辐射的遗体完全隔绝开来。图为一名1999年,一名乌克兰小女孩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逝去的消防员墓前悼念。REUTERS
幸存下来的“清理者”则面临长期的健康困扰,他们的一辈子不得不在没完没了的医疗辅导中度过。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对“清理者”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切尔诺贝利“清理者”受到的辐射相当于衰老10年或者长期吸烟造成的危害。但你永远不知道将会面临何种健康风险,以及其与辐射的关系到底有多大。而这也是核灾难的恐惧和争议所在。图为一名直升机飞行员“清理者”在接受医疗辅导,这样的检测他已经历多年。
图中右侧是为切尔诺贝利“清理者”们颁发的勋章,上面的图案是一滴血被α射线、β射线、γ射线穿过。
在国外一个网站上,有人问:哪些成就可以称之为人类最伟大救赎?有人回答:瓦西里·阿尔希波夫、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夫分别在1962年、1983年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的消防员,大屠杀期间帮助犹太人的人。图为一座消防员纪念碑树立在切尔诺贝利,纪念“那些拯救了世界的人”。
如今,一个的新的石棺在四号反应推旁边兴建,因为旧石棺出现裂缝,仍在释放核辐射,这个圆拱型的新石棺在附近建好后将平移至反应堆上方,据说可以管100年。然而,部分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长达几亿甚至几十亿年,如铀238的半衰期为45亿年。谁才能完全“清理”这些核辐射?
小T综合自:腾讯网
如果爱∣请长按

欢迎加入互联网科技交流群请加小助手微信:lanmeitmt
来这里找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阅读原文阅读
加载中